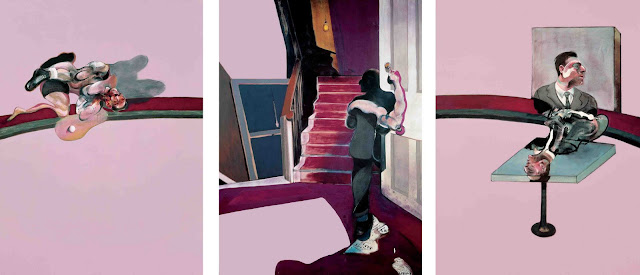想想每個時期的朋友,大家目前似乎都過得安好。找到了某個屬於自己的位置,即使徬徨不知所云,日子還是默默的過去,生活還是靜靜的到了今日。
微微笑,每當意識流裡劃過記憶裡朋友的種種荒誕;微微笑,每次不經意的看到熟悉的環境或是曾有過留戀的場合。就算是一張啥麼激情成分都沒發生的相片,看到在生命中曾經站有過某個位置的朋友,我還是會忍不住,微微笑,芭樂又不免俗的想:他現在在幹嘛?!甚至更矯情的:他過得好嗎?!但也常常之後伴隨著:我跟他從前其實也沒有很熟嘛!多麼無情的自己阿~
也許這是跟我熟識的朋友常會有的想法(我自作多情的這麼想):多麼無情的劉彥呈。因為我不習慣人多的聚會場合,即使是一群熟識多年好朋友,不管是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或是工作時的同行與同事,只要超過某個限度心裡就會開始產生狼狽感,是我唯一在價值處世觀上的潔癖:必須在任何細節與生活態度上不管具象抽象與否,維持一定感覺上的"優雅",以文青的方式來說,狼狽會殺死我的靈魂,相信我的某公務員友人會體會這樣的靈魂說。當我開始覺的交往語說話的對象並沒有真誠或是實在的說話時,我開始感到狼狽,因為太多喇賽與垃圾話充斥著寵個空間,當然我依舊會參與與玩的不亦樂乎,只是內心深處那道感性是很誠實的。我也常跟朋友說,無法接受太多人一起的聚會場合,我會不自在或是覺得我的空間被侵入的太雜亂。所以缺席了許多朋友的聚會,拒絕了許多次朋友的來訪,因為我需要一個自己可以掌控的空間,我也需要一個自己能盡情失控的空間,這空間其實狹隘,我常為此容量不太而對朋友們感到抱歉,這些話也很難對著一個人數眾多的聚會說出,因為會有更多的慰藉與安撫效果隨之而來,那是令人來不及一一誠心接受的速度,像在line上面的對話一樣,一轉眼就產生了排山倒海的對話與內容發展,快的眼睛與腦袋都跟不上的僅能捕捉隻字片語在自己的腦海裡即時建構出那一件啥麼樣的事。
看著朋友們一個個處在自己銘刻的空間,以當下屬於自己的語言去處世交往,我由衷的覺得開心,將心比心之下感到幸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以某種姿態活著,也許是專業與興趣、也許是經濟與生活、也許是在邁向未來、也許是在本島之外的海外學習與工作。。。大家在這個世界都適得其所,即使不常見面,但能恬靜的想到朋友們各自的現況,真的會忍不住,微微笑。非常妙,也還不足以形容每次聽見朋友們近況的大小事,不管是感情或是家庭上、還是事業或學業上。。。微微笑,真的是非常妙。。。。友誼總是在孤獨與寂寞的極端之時感到最強大,生命的弔詭總是如此,必須說服役的新訓專訓以及現在在單位上也出現了這樣一些人,一些會使得忍不住持續微微笑的人,而且非常妙。
我愛我的朋友們,我喜歡個別和朋友們相處的時候,我也必須時常使自己處於獨身與隔絕的空間。當不經意的交會或是想念來臨時,我想我會給朋友一個真心的擁抱,問候一句最近過得好嗎?!
微微笑~重逢話家常
I
MISS YOU ALL, MY FRIENDS